济南中学的红砖墙上,六月的爬山虎正攀着窗沿生长。高三最后的日子像被汗水浸软的速写纸,褶皱里藏着47分的数学卷、画室未干的颜料,还有错题本上,老师用红笔点亮的细碎星光。 集训回来那次月考,数学47分的卷子像块铅块压在心头。晚自习对着错题本愣神,抄题、照搬答案,却连错在哪儿都摸不清。第二天本子发下来,函数定义域旁立着红笔小字:“注意写当且仅当!”往下翻,歪斜的改正处爬着道绿箭头:“达子,最近状态特别好,保持!”后来才知道,张老师常抱着我们的错题本在办公室待到深夜——那些批注早记不清具体字眼,只记得他把我叫出教室时,说“美术路难走,咱文化课托底”的样子,像冬夜把冻僵的种子揣进怀里的人。 物理李老师的打印机总在课间嗡嗡响。我刚回校时,他把一摞复习资料塞给我,纸页边缘还留着他手写的批注:“这个公式画重点,艺考回来的同学多看看。”高考那两天,我没顾上吃午饭,在校门口撞见来送考的他和张老师。张老师把三明治往我手里塞:“不吃饭哪有劲考试?”李老师嘴上催“快进去吧”,手却攥着我的准考证看了又看,那“老父亲”似的笑,比考场外的太阳还暖。

地理课总飘着王老师的济南话:“咱就是说能别说话了不?”可我问问题时,她立马收了玩笑样,红笔在答题卡上圈出失分点:“这里等高线判错了,来,咱重画一遍。”后来我的地理答题卡总染着片红,那是她把每个漏洞都刻在心上的痕迹。 政治王老师的蓝色活页夹磨出了毛边,里面夹着三年时政热点,“依法治国”的页签都快掉了。她腿受伤时拄着拐来上课,每节课仍叫我回答问题,晚上考的卷子,转天早上就带着红笔纠错回来——我零散的知识点,就是这样被她一点点串成了线。 “你别把自己当艺术生,就当和大家一样。”语文陈老师总这么说。我考砸时去找她,她翻出本泛黄的作文集:“你看这篇,和你现在多像。”后来我在基础知识本上写满批注,作文素材堆了三本,终于懂了她常念的“粗缯大布裹生涯,腹有诗书气自华”,原是给迷茫人的船桨。 英语办公室的灯总亮到九点。张老师总在晚自习后叫住我:“阿达,这个语法再讲一遍?”她给我编的习题册上,每题旁都画着小笑脸;离校前最后一次听力,耳机里没了熟悉的录音,是她和同事们的声音:“等你好消息呀”“别慌,正常发挥就好”——那一刻才发现,那些深夜亮着的灯,早把我们的路照得亮堂堂。 清理课桌时,桌膛里翻出六样东西:数学错题本上的红绿批注、物理资料上的“重点”记号、地理答题卡的红笔痕迹、作文集里的折痕、政治活页夹的旧页签,还有英语卷尾的小笑脸。它们在夕阳下叠在一起,像济中的微缩景观——原来老师从不是站在讲台的“教书人”,是把我们的迷茫收进衣兜,换成一把把种子的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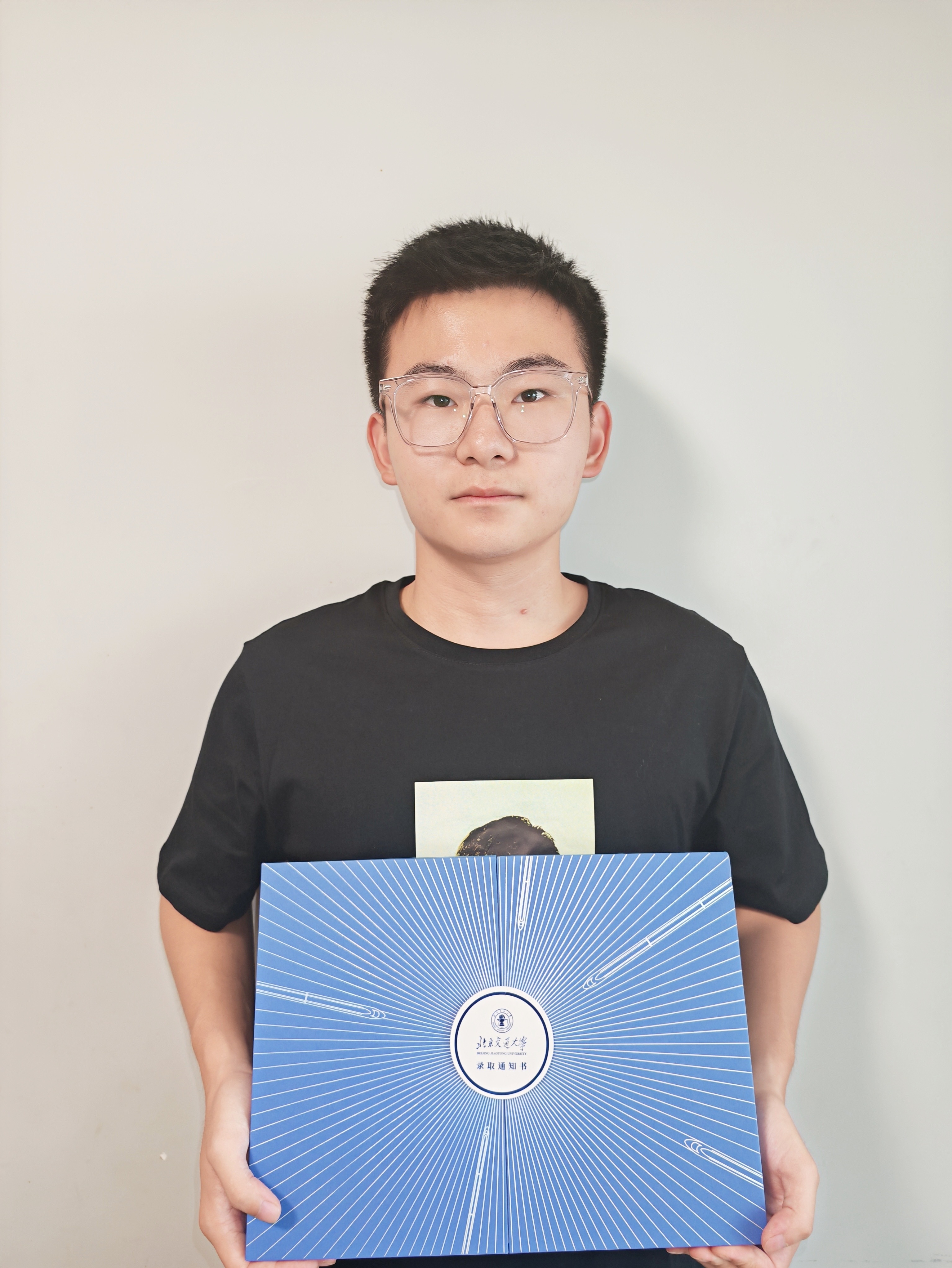
如今红砖墙的新叶又在颤动。我知道那些曾掷向我的微光,终将在未来的图纸上长成梁柱。因为所有俯身的浇灌都不会白费,就像董亚校长镜头里,晨光中倚着电梯读书的身影,早把“敦品笃学”刻进了年轮;就像那些日夜陪伴的老师,把“务本求实”的温度,烙成了我们走再远也忘不掉的底色。 风过爬山虎时沙沙响,像在说:你看,那些种子,都发芽了。
|